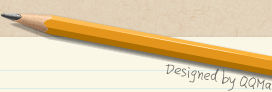罗大佑:算了吧,这个太可怕,我就是开个演唱会,唱歌、拿钱,不拿钱就跟他们吵,这是个工作,不是精神偶像。尤其是媒体里面弄出来的这种高帽,什么音乐教父,我听到自己都会笑。
编者按:他,是一个音乐人,创作了很多经典,也成就了自己歌坛常青树的传奇。他又是一个深隧的思想者,他的歌曲不是矫情的呻吟或麻醉的狂欢,关于政治、现实与人生,有人用文字犀利表达,他用歌曲巧妙演绎。不管哪种方式,都“是时代的一个出口”。推荐各位网友看《南风窗》专访,一起认识谈音乐的罗大佑,谈政治的罗大佑,感性的罗大佑,博学的罗大佑,在音乐中行走的思想者——罗大佑。
2011年9月26日,罗大佑在北京接受了《南风窗》记者专访。
“现在不用再high了”
《南风窗》:我去过两次台湾了,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,2009年9月20晚上在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生态村,台湾音乐人协会理事长陶�带了一批台湾音乐人在纸教堂前面演唱,纪念台湾9•21大地震10周年,观众席地而坐,与音乐人零距离,互相感动。您也这样下去过,对吧
罗大佑:对的。正好今天是9月26日,1999年9月26日我从纽约回到台北,地震后5天。这场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因为很多在地震中死了,去看看情况,了解一下灾情。唱唱歌,总是唱跑调。我是台湾出生的,在我5岁的时候就曾遇到地震,我们睡房在5楼,母亲拖着我们小的就往下跑。忘不了一个母亲带着3个小孩往楼下冲那个感觉。我们是在地震中长大的,但大地震来的时候,谁都没有办法去很冷静地面对。
《南风窗》:灾难发生的时候音乐可以抚慰心灵。
罗大佑: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。那时很多人很惊慌,惊慌了3个月才定下神来。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去埔里地震灾区视察,其中一架直升机降落时一下子就撞倒了树,树被撞倒后又压死了一个女孩。大灾难来了一切都是很乱的。
南风窗》:刚才的问题打开了您的记忆。所以现在有很多评论说,罗大佑很宏观、很意识形态、很历史,年轻人都听不懂了。
罗大佑:我们经过的历史其实蛮长的,他们没办法直接懂,也正常。我需要的就是和我一起成长过来的人,由他们去跟子女“翻译”,他们带着子女来看我的演唱会,这个可能比较实际一点。
要让我直接告诉80年代这些小朋友的话,我觉得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方式、我们唱的歌——说起摇滚乐,他们就觉得摇滚乐像恐龙时代音乐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个翻译者,有个解释人在中间,这就是时代的变化。
《南风窗》:您想告诉这些翻译者的是什么?
罗大佑:我现在在读一本书,意大利作家依塔罗•卡尔维诺的《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》,这是一本蛮有政治性的书。音乐现在也算是很没落了,大家都知道不像以前一样,文学也更糟糕。这本书告诉人们文学是最基本的,无论人到哪里去,都不能没有文学。在被各种表演的媒体给踩下去以后,文学在这个时代可以发挥的作用更大,文学家会发挥出更大的想象力去把文学的使命传递下去。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。《南风窗》:我们注意到,这次演唱会现场最high的时候,观众并没有跟您high起来,您会不会感到失落呢?
罗大佑:high起来是那个年代的摇滚音乐,但我唱的是慢歌,这歌是1983年出的唱片,已经28年了,这些听众其实是在回顾这首歌的历史。 当初他们是年轻人还在谈恋爱,现在已经当上了爸爸,他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孩子变成电脑儿童。
摇滚最辉煌的时期过去了,电脑充满每个人的生活空间。我就是想带大家在现实的状态下,跟我们回到过去的年代,不要忘了这些古老的乐曲。
《南风窗》:传递给“老朋友”们这种感觉,除了怀旧,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?
罗大佑:年轻的这一代可能得多花时间去想想人的本质。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。可能因为我没有小孩子,我不知道很多父母对小孩子的担心,可我看见的小孩子学业都很重,压力都很大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小朋友,他已经受不了学业的压力都跳楼了。
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点老师在教训学生的感觉?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孔子把仁讲得非常好,设身处地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现在我们人和机器在相处,至少是通过机器在相处,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很少,这其实是蛮大的问题。科技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让人远离自然,远离人性。
“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”
《南风窗》:今天的罗大佑听起来一点也不愤怒了,是不是年龄大了,愤怒不起来了呢?
罗大佑:要看怎么解释愤怒了。
《南风窗》:当初在台湾,罗大佑可是激烈批判现实的。
罗大佑:就是1982、1983年,主要是那时候社会比较封闭,所以出现像罗大佑这样的言论,大家会觉得是在批判。你把罗大佑当初讲的那些话拿到现在来看,谁理你啊,尽讲这些,这样还算抗议?
当时我讲的那些,比如台北不是我的家,其实那真不是我的家,这哪能算抗议?那个时候太封闭,我自己还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医生,也没有那种拿这个当饭碗的感觉,自然也不会考虑这样讲话会不会丢掉工作,没有这些压力,就比较敢讲,仅此而已。
《南风窗》:当年你们那代音乐人有没有一种集体的自觉意识,要去呐喊改变这样一个沉默的年代?
罗大佑:集体大概不会,集体那就叫革命了。我基本上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音乐人,当社会里很少有人讲的时候,我出来讲一讲。现在那么多人讲,每个人都在骂,还需要我讲吗?基本上音乐对我还是比较重要,我写好听一点的歌比较重要。
《南风窗》:在我们的印象里,华人世界的演艺明星中,您可能是最热衷表达严肃命题的一个了,这跟你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台湾民主运动是不是有很大关系?
罗大佑:台湾民主有幸,但也有很大的挣扎,血泪汗水的挣扎。我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,在对与错之间,在民主和专制之间,一路挣扎着摸索过来。我们看着他们折腾,发生多么大的事情,也不敢出声,最后只好在文学、歌坛上面表达一些声音。
我用歌声表达,龙应台用她的文学表达,这都是时代的一个出口。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出现在1979年,也告诉我们要用这样抗争的方式去争取。像施明德在美丽岛事件被抓进去,其实他刚被关了15年,才出来3年而已,又被抓进去,那才是真正的厉害。
我1985年离开台湾时,也是满身伤口,国民党觉得这个家伙很不听话,对我的表达方式不开心。还没有成立的民进党也对我不开心,他们觉得你怎么不是在替我们讲话?所以你不是什么抗议歌手。
什么时候我变成抗议歌手了?我从来没讲过抗议这句话。我们是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,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。
《南风窗》:但是政治很敏感的。
罗大佑:政治无所不在,我觉得我的东西是在抵抗政治。我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,“统派”帽子我已经戴了多年,是他们(台湾绿营)给我的。我更想说的是,音乐人绝对是反战的,反饥饿的,音乐人的希望就是唱歌。温饱以后才有音乐。你看60年代那些嬉皮,就是反战的。
《南风窗》:是不是1985年的政治压力,影响了你后来的选择,让您刻意要离政治越来越远?
罗大佑:不是,这是我自己不喜欢,因为完全透支了,我在台湾觉得就搞不下去了,所以我自己就完全淡出了乐坛,逃离那种环境,应该是一个自我放逐,完全丢掉那些掌声和鲜花。
承担责任
《南风窗》:过去这些年,您在大陆做了不少事情,比如和李宗盛他们组合“纵贯线”,到处开演唱会,有什么收获吗?
罗大佑:真正的成果是聚集了一批音乐人,在2008到2009年的金融海啸时,证明音乐还是有一些力量把社会上消极的气氛打消,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正好在这个时候“纵贯线”出现,也不晓得它为什么谈成了,但是它的余波到现在还没有消失。
人类的生存状态本身大部分都属于政治和经济的范畴,当歌舞升平、精力很好的时候有一种玩的状态,在很不好的时候,音乐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另外一种状态,真的去承担某种责任。
《南风窗》: 除了年龄上的区别之外,大陆的罗大佑和台湾的罗大佑有什么不同吗?
罗大佑:为什么几十年前的罗大佑那么愤怒,现在不愤怒了?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,不是一个抗议者、愤怒者,我不可以永远是个年轻人,既然是音乐人,在一个大家拼命骂、对抗的时代,那我写一些好听的歌不是对的吗?所以我告诉自己,现在应该写一些好听的歌。
《南风窗》:这几年,在您的音乐中,关于大陆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东西吗?以这次的“2100恋曲”演唱会为例,我看到你们有5个颜色的创意,可是,“红色”段落的探戈,展现的是夜上海的纸醉金迷,“绿色”段落则是以台湾原住民音乐为基调,这看起来挺混乱,您到底想传递什么信息?
罗大佑:我在表演里面用的是张爱玲的《海上花》。张爱玲是从那个年代的上海出来的。在租界时代,上海纸醉金迷,鸦片、娼妓、乱七八糟的投机。那也是一个逃难的时代、战争的时代,人们妻离子散,最好和最坏的东西、人性中最光辉和最丑恶的都在这个地方发生了,那种血淋淋的本性本身就是红色的。
而现在,到上海我喜欢住外滩的和平饭店,看到很多老人在老街上跳舞,跳得很开心,那种热情也是红色的。和平饭店舞台上表演的都是年轻人,他们的摇滚音乐也是热情的,另外,你看街头那些可怜的劳工,烈日当头,满头大汗,那也是年轻的血泪汗,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血的,红色的。这些才是整个的都市感觉。
《南风窗》:今年是辛亥百年,联想起来,当年很痛苦,有血泪,但也恰恰是我们从专制走向民主,走向自由社会的阶段。您是要重新怀念这个东西吗?
罗大佑:我觉得不是怀念,辛亥100年我觉得是非常不易,我总是觉得人不要忘本。北京奥运会,上海世博会,广州亚运会,深圳大运会,都是得之不易的。现在仿佛任何人都觉得很辛苦,但最起码现在我们真的是比10年前要好,你们现在还不够幸福吗?当年在台湾我是“禁歌第一名”,我知道今天的东西得来有多不易。像现在开演唱会我没有送批文,没那么困难的,当地就搞得定,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
《南风窗》:那绿色呢?您想通过这些章节表达些怎样的严肃意义?
罗大佑:绿色其实都是我们的梦。不客气地说,台湾原住民其实都是被赶到山上去的。能住平原,谁愿意住山上?闽南人迁到台湾以后,跟原住民混在一起,因为汉族人比较多,会团结,就把他们赶到山上去了。汉族人则利用土地开发,做什么房地产、商业,都在远离土地。
这部分在我的演唱会中,是想说人要到大自然中,人类跟科技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,在生活里面多制造一些绿色的气氛。像日本的核电,还有7•23动车追尾事故,都是惨痛的教训。国家发展太快了,非要追求什么都是第一名,没必要,一个大国,还追什么呢?如果再这样快下去,肯定是10倍20倍的代价。
都市流浪
《南风窗》:您的歌里有一股浓浓的乡愁味,比如《错误》、《乡愁四韵》,台湾在您生命当中是什么地位?
罗大佑:一直很复杂、一直很矛盾、一直都是爱恨交加。出生的地方自己没法选择,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。人旅行要去哪里,住哪里都可以选,但是出生的地方你不能选,就是这样。所以,我还是很爱很爱台湾的,没办法,因为在那个地方成长了很久,出生一直到20几岁都在那里,只是我不习惯把“爱台湾”挂在嘴边。
《南风窗》:从纽约回来后,您没有选择在台湾久留,却去了香港做音乐,为什么?
罗大佑:台湾我不想回去, 我觉得那个地方对我来讲,政治味太浓了,大家对我的压力太大,要求太多,说罗大佑不为他们讲句话,就像罗大佑背叛了他们那个党的精神一样。去香港做音乐,只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地方。
香港很有制度,你写歌就有现金,香港作家作词协会很多,他们自然会帮你收取这一部分的费用。另外,香港虽然小,但是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人比较守法,也是制度会让人守法。最吸引我的一点是,香港英雄不问出处,完全靠自己的能力。在香港要很货真价实才行。
《南风窗》:北京呢?这个城市对您的音乐和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
罗大佑:其实我2002年就到北京住过一年半,我很开心,我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吸空气。这种空气是一种能量,这个地方建都1000年,过去10年是1000年来最戏剧化的,很多东西全部拆掉重盖,显然是有一种很大的能量,所以我觉得呼吸蛮重要的。
不过,作为一个外来者,我只是看大局,能感觉到的是这个都市有1000年来的官僚文化沉淀其中,曾是最官僚的一个都市,这几年洗涮得比较多一点,现在好了一点。当然,如果放到地球上的位置,它变得还不够。
至于我的创作,以前我在北京会写不出曲子来,这几次住在北京我觉得能写出曲子来了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,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,觉得旋律在跑,在睡梦中也会有一些旋律、一些新的东西在跑,醒过来会想把它记下来。我甚至有习惯,因为现在手机方便了,都有录音功能,我觉得这个旋律还是新的话,我会把它录下来。我发现录的东西有新的感觉,也就是说,对这个都市开始有了音乐感觉。
《南风窗》:是您更熟悉北京以后这些东西出来了,还是北京的变化让这些东西出来了?
罗大佑:在这个地方睡觉时,我整个人是放松的,睡得很安稳,我觉得可能跟季节也有关系,因为现在是秋天。然后大家都忙,现在人高度分工,很忙,很有效率,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,空气里面就有一种空间出来,作曲的人不会觉得隔墙有耳,不会在你谈话时旁边有人在看,那是罗大佑啊,那是不是周华健啊,我们有这样的空间,在这样的空间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都没人管你,这个空间很舒服。
以前我觉得北京这种空间很少,别人很容易侵占你的空间,现在我觉得大家要管好自己的那部分都来不及,所以没有时间去侵占别人的空间了。
音乐与家国
《南风窗》:当大陆越来越有空间的时候,那么多台湾精英都到大陆来,您会为台湾的前途感到忧虑吗?
罗大佑:我倒不会忧虑,这不是跑到大陆来的问题,只是说现在多一个地方可以跑。罗大佑当初跑到美国去,他会再跑回来,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资历,需要学习,需要养分,像龙应台也是一样,来来去去。
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岛,一个小岛能有多少资源?台湾有想法的人应该往外跑,把外面的经验、理念带回来,变成台湾的独特经验,然后再交换,再去外面带资源回来,变成一个继电所一样。不要担心人跑掉,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能再把人拉回来,还担心什么呢?
《南风窗》:我们聊聊音乐本身吧。细听过《皇后大道东》、《原乡》、《首都》之后,我们会发现很多旋律都是一样的,只是您分别用国语、台语,或者粤语添上不同语言的歌词。有人质疑说罗大佑偷懒,您却认为是一种探索?
罗大佑:我是在逆向追溯语言之间的共通性,把语言本身丧失的一种东西找回来,有时候你用同一首歌表达不一样的语言时,会到忘记这是同一首歌的地步。好像我有一首歌叫做《再会吧,素兰》,那个听起来你会觉得整个人被拉到另外一个空间里去,我喜欢那种时空错乱。在一个太工整的时空里,做艺术的人偶尔制造一些时空错乱的感觉是好的。
听旋律完全是同一首歌,但是因为语言会变得差异极大。我就会去想从当初那些相同的语意到现在,中间经过了多少时间的演化,是谁主导了这些语言的改变,这个一直是我最大的困惑。
《南风窗》:这么多年下来,您对音乐价值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?
罗大佑: 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乐排第二个,是有道理的。歌曲在社会里面必须要担任一种教化的功能,我说罗大佑的歌曲里面不能没有信息,就是这个意思。从广播时代开始,一直到有唱片这样一种媒体,让我们可以赚大钱,音乐的力量很大,力量大的时候就必须注重这个工具,必须要能够跟观众互动、教化,没有这个功能我就不唱,这是我一定要坚持的。
《南风窗》:那作为一个音乐人,您有更大的野心吗?比如有媒体说您要做精神偶像?还有音乐教父等等。
罗大佑:算了吧,这个太可怕,我就是开个演唱会,唱歌、拿钱,不拿钱就跟他们吵,这是个工作,不是精神偶像。尤其是媒体里面弄出来的这种高帽,什么音乐教父,我听到自己都会笑。
我18岁就开始开刀了,我太清楚一刀下去人血淋淋的,人太脆弱了。音乐圈我入行蛮早,进出乐坛那么多次,我看到太多人起起伏伏,你要我冲昏头太不容易了,再大的掌声、再大的欢呼声喊罗大佑,都不会让我冲昏头,我知道那是个假象,是观众需要那个感觉,不是我需要那个感觉。你要是被那个东西冲昏头的话,只能说你还不够资格站在这个台上。
《南风窗》:那对国家呢?像您这样一个在台湾、美国、香港、大陆多年游走的人,怎么理解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字眼呢?
罗大佑:我相信人相似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,尤其当你同样一种语言,同样一种背景的时候,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的可能性更大,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音乐的目的,一首歌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,能够引起共鸣的人越多越好,我们不是在做一个拆散大家的事情。
(来源:节选自《南风窗》杂志)